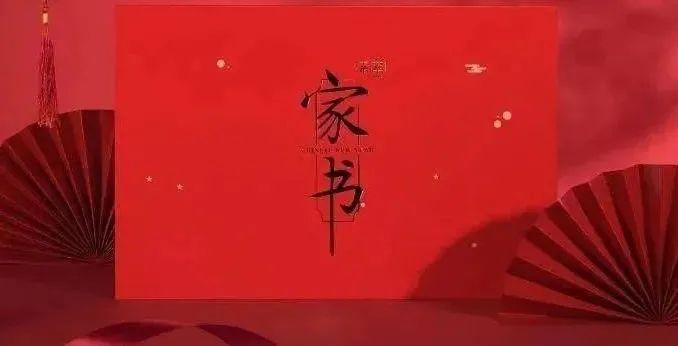作者:潘五一 播音:冬 梅
我曾是一个老病号,知道什么叫疼痛,什么叫平安;看清什么叫世态炎凉,什么叫同病相怜;什么叫陌路和冷漠,懂得什么叫亲情和大爱。
在住院期间,我看见一个个清一色的白衣匆匆行走在患者的病床间,工作在不分昼夜的岗位上。
她们将自己的青春与病人的病痛连在一起。这个患者要打针,那个患者要挂水;这个患者刚做完手术要注意观察,那个患者病情又有反复要特别留心;深夜又来了急诊要紧急抢救……心里再也顾不上自己,多的只是对病患的一份牵挂。
当她们听到病房传来均匀的呼吸,当她们看见病患香甜的安睡,当她们目送一个个康复的患者,从一张张微笑的脸庞、一次次诚心的谢语中,她们也得着满满的安慰。
三十多年前,我生病住院。我遇见了一名实习护士。由于反复扎针,被病人和家属埋怨,拒绝,甚至辱骂。但她还是以耐心的态度解答病人的问题,以笑脸面对家属的误会和刁难。我看见她受了委屈在没人的地方偷偷落泪,又很快回到工作岗位。
她在我手上扎针,本来就特别怕痛的我,有时当场疼得冒出冷汗。我也有些抱怨,但我还是强忍疼痛装作微笑:“不要紧张,不行,可以再试一次。”有几次左手扎不准换右手,手不行换脚。她有些慌张和埋怨。我说:“不能怪你,是我太瘦了,脉管太堵太细不好扎。”
面对我微弱善意的一笑,她的心里荡漾起涟漪,满了感激,晶莹的泪光湿了微笑的眼角。
我明知她扎针很痛,但我还是莫名其妙地指望她来扎针,直到后来病得痊愈,还想再生一次病让她来扎针……
当她来通知我出院的时候,我心情特别的失落。我是多么想在医院里再住一些日子,可我怎么好意思提出这种荒唐可笑的请求呢。
时隔几年,我还真的生了一场大病,需要动手术。她再来为我扎针的时候,不再是一名怯生生的实习生。
她扎起针来,已是信心十足,心灵手巧。一双纤纤之手,在我枯燥干瘪的表皮上践行救死扶伤。细致的针,轻轻地走进了我的血脉;一滴水汇成生命的泉源,柔柔地流着滋润我的心。那星星点点的针疤,如一朵朵生命之花,在我心间美丽绽放。
在动手术的那段没有亲人在身边的日子里,我成了她的牵挂。她就像亲人一样,常常守护在我的病床边;像爱的天使会伴随身旁,守护我的寒冷孤单。我感觉到她是一名充满爱与温柔的护士,是一位白衣天使真实的存在。
她总是步履匆匆,来到我的病床边,问我好点了没有。她握着我冰凉的手观察,我感觉到她的手也是凉凉的,如软玉一般温柔;她天使般的眼眸抚慰着我手术的伤口,我感觉伤口痒痒的,似乎在慢慢愈合。
在那麻醉迷迷糊糊不能动弹的日日夜夜,她以柔软的身躯为我挡住病魔,用纤细的手指为我驱走病痛。她一次次搀扶着我越过病痛,越过死亡的阴霾,进入平安温馨的梦乡。
她一身轻云般的洁白,展现一个白衣天使的圣洁;胸襟上小小的红“十”字,传递着爱的信息;面对我渴慕痊愈的目光,她的眼神传递生的希望。她的关爱,如春雨浇灌我饥渴的心,又如甘泉润泽我忧伤的灵。
她目睹无数的生离死别,深悟生命的可贵。每当我呻吟需要呵护时,她总是第一个时间来到我的病床边。她不求什么,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求。
在那段我一生中最痛最孤单的日子,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平安与亲情的同在。她走近我病床边轻盈的脚步声和墙壁上天使般的身影,都能为我疗伤。
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的女孩。我看见她最美的脸,最美的心,最美的身影,连她手上的那根针都如此美丽。
有一次,她休假,换上便服去看我,我差点认不出来。我感觉到她像家人一样,有亲人的感觉和家的味道。
在一次聊天中,她问我认识南丁格尔吗?我说我没听说过。于是她就跟我讲南丁格尔的故事:
1853至1856年间,克里米亚半岛爆发战争。一名护土带领38名女性志愿者奔赴前线。
每当夜幕降临,一个“白衣天使”就提着一盏小油灯,沿着崎岖的小路,去4英里外的营区。
她从每个病床一一走过,看见平安的伤员,她便投去天使般的微笑;面对痛苦呻吟的病号,她便带去慈母般的安慰。
伤员们远远地看见她缓缓走来,那修长的身影被灯光反投到墙壁上。伤员们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,亲吻她那浮动在墙壁上的身影;也有伤员在看她离去时,就匍匐在地亲吻她的影子,然后躺回床上进入安息。
她走到哪里,哪里便有了生的盼望。在伤员的心目中,她就是守护生命的天使!
她从小就怀有一颗怜悯之心。她看到受伤的流浪动物,都会伤心落泪;看到患病的百姓,更是悲悯至极。
在她懵懵懂懂的年华,听见一个来自世界之外的声音召唤她去护理伤病的生灵……
从那时起,我才知道她给我讲的那个护土,名叫南丁格尔,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护士。她问我爱南丁格尔吗?我说南丁格尔是个好护士,她也是个好护土。
后来,她还给我讲了石美玉、林巧稚、特蕾莎的故事,她们和南丁格尔一样,一生都是“爱”,她们都没有结过婚,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护理事业。
她还给我传递“爱的信息”。病中的我,迷迷糊糊,似懂非懂,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,不明白她说的到底是什么。但我想讨她的欢心,不懂装懂。她还问我愿不愿意相信和接受“爱的信息”?我说她愿意的,我也愿意,那样我可以去关爱病人。
直到几年前,我才知道什么是“爱的信息”,我也信了,接受了。原来,她早已是我灵里的姊妹。
三十年过去了,一直没见过面。一天,她的身影忽然出现在我面前,霎时就不见了。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,就去找她。
在一位老保安那里打听到她还在那个医院,又在一位护士那里打听到她出差了。我问那位护士有没有她的电话号码,她说不知道,别人也可能不愿意告诉一个陌生人。
后来我又去打听,没人告诉我。后来,我还去过几次,一直没看见她,或许我只是她曾经的一个病号,也就又敢多问。我放心不下,又常常去打听消息。
后来无意中听见医院的护土说:“想不到她去了武汉,就再也回不来了……真可怜,干了一辈子护士,连个爱人子女都没有……”
我知道,她已经去了一个没有苦难和眼泪、没有疾病和死亡的地方。
在模糊的泪光中,我依稀看见她被汗水浸透的衣衫,被雾水打湿的护镜;看见她脸颊淌汗,睫毛凝霜,痕迹勒脸……看见她天使般的身影,印在病房的白色墙壁上,印在病床白色的床单上,印在我破碎的心上,印在我不死的记忆中……